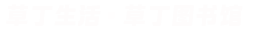2013年12月,几内亚的梅里昂杜村,一个两岁的男孩,感染埃博拉病毒去世。随后,病毒席卷了塞拉利昂、利比里亚。2014年至2016年,几内亚确诊3811,死亡2543;塞拉利昂确诊14124,死亡3956;利比里亚确诊10675,死亡6809。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肆虐横行,成千上万的人感染并死去,平均病死率达50%。
《血疫》之后,非小说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带来了新书《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直接抨击了席卷西非的瘟疫,回顾了1976年的危机。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来源于作者的数百次个人访谈和对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档案和原材料的多年研究。书中的人物鲜为人知。然而,在世界生命中最具毁灭性和最迅速的瘟疫的中心,我们总能看到他们的行动和选择,生存和死亡。希望读者能以此为窗口,看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埃博拉流行病更像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新发病毒跳出生态系统后造成的震荡波。病毒在人群中自我增殖,吞噬生命,遭遇人类这个物种的反抗,最终偃旗息鼓。然而,下一个震荡波会是什么?
如果一种新的四级病毒传播到北美或任何大陆的数百万人,医院能处理这么多病人并照顾他们吗?如果感染人数超过百万,流行病学家能否追踪并打破感染链?世卫组织称,2014年埃博拉疫情表明,“世界尚未做好应对严重流感大流行和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准备”。这似乎也适用于我们将在2020年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西非疫情中,新感染的医务人员人数居高不下。截至2014年底,有近700名卫生工作者受到感染,其中半数以上死亡。这种病毒是个真正的恶魔,它随着忠诚和爱的链条传播,正是这样的情感将医院的医护人员彼此连接在一起,最终连接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他们是挡在病毒和你我之间的一道薄弱的防线。
埃博拉战争不是通过现代医学赢得的。这是一场残酷的中世纪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普通人,另一方是生命形态。它想以人体为生存工具,活几亿年。为了打败这个非人的敌人,人们必须除去他们的人性。他们必须克制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和本能,撕开爱情和感情的羁绊,孤立自己或亲人。为了拯救我们自己,人类必须变成怪物。
非洲西部不存在类似于刚果盆地的远古法则那样的习俗。然而在2014年,人们与埃博拉的交战法则完全就是1976年让-弗朗索瓦·卢泊尔医生站在市场案台上推荐扎伊尔人民使用的方法。病毒通过接触体液传染。假如你学会识别症状,不去触碰体液,避免接触出现症状的那些人,放弃处理死者,你就能保住自己不被感染。
现在,守卫病毒圈大门的战士们都知道,他们面对的敌人是可怕的,这场战争必然会旷日持久。他们的许多武器最终会失败,但其他武器会开始工作。人类在这场战斗中有一定的优势,拥有病毒所缺乏的一些要素,包括自我意识、团队作战能力和牺牲意愿。
既然病毒可以突变,那么我们也能改变。
卢波尔医生为了救孩子忘记了病毒
摘自《血殇》,有删节
理查德·普雷斯顿|姚祥辉译
当米里亚姆修女在恩加里马医院去世时,一位天主教修女联系了金沙萨一位名叫让-弗朗索瓦·卢波尔的医生,请他帮助研究这种疾病。当时,卢波尔博士38岁,领导着比利时政府在扎伊尔的医疗援助组织:热带医学基金会。卢珀个子矮,下巴尖尖的,眼睛是蓝绿色的,他的脸被阳光和雨水晒成了热带棕褐色。他有一头浅棕色的卷发,以脾气暴躁而闻名。Lupor的家在商业区,是位于Mf Mulutunu大道上的一座刷白的石膏房子。他和妻子约西亚·维斯索奇以及两个年幼的女儿住在一起。作为比利时医疗组织的领导人,他管理着在扎伊尔各地工作的大约200名医生。
推荐阅读
- 贝吉塔和布玛 龙珠异次元:贝吉塔与布玛一见钟情 弗利萨的帝王梦破碎
- 明日方舟俄乌事件彻底火了,对于游戏里的乌萨斯你了解多少?
- 乔可拉特 谁是JOJO当中最肉的反派 铁打的恋人也称不上是最硬
- 《明日之后》乌萨斯的真实原型是什么?
- 谢洛托 世界足球最强兄弟是谁:广州恒大主帅上榜 巴萨最强双胞胎
- 皮克 巴萨主席宣布巴托梅乌辞职 皮克:天亮了 太阳重新升起来
- 哈萨克斯坦美女 世界女排有哪些颜值极高的美女 她们的现状如何 萨宾娜有点可惜
- 卡萨关注20位职业选手,包括RNG五人TES五人
- 萨娃 梦想成为网红的美女 迪娜·萨娃的成功对你有帮助吗
- 年五来袭萨瓦图恩谎言被揭穿《命运2》守护者集结为光能而战